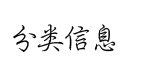大家好,歡迎收聽早茶夜讀之小說民國,我是楊早。這周我們共讀的作品是蕭紅的成名作《生死場》。
幾年前,由于《蕭紅》和《黃金時代》兩部電影的上映,蕭紅一度成為熱點話題。當時我們做《話題》也曾經(jīng)做過關于《黃金時代》的文章。但是大部分人的關注點——包括這周李子和綠茶——都在解讀蕭紅的生平。李子和綠茶談得很好,但是我看著是有點疲勞了,因為蕭紅的生平,對我來說,已經(jīng)是嚼過很多遍的饃了。
前面土城談到“不敢讀蕭紅”,其實也是繞著說,反而邱小石提到了《都靈之馬》,是他自己的解讀,因為那部電影我也很喜歡,影片的調子,可能跟蕭紅的《生死場》里面那種陰郁、慘烈與絕望,其實是有相通的地方。這一點我是認同的。再往前就是白水,還就是他一如既往的點評式的詩意化的解讀,反正大家可以參考。
《生死場》是一部老作品了(你也可能稱之為經(jīng)典),可能你也看過田沁鑫的話劇《生死場》,雖然彩聲無數(shù),我覺得那真是簡化得很厲害。
我們怎么去讀《生死場》?這次重讀,我選擇了一個cosplay的視角——我覺得有些新的東西,可以倒過來讓我們借鑒一下。
請你設想你自己就是在1935年的11月14號,天氣跟現(xiàn)在差不多。假設就是這一天的夜里,你是魯迅,你在燈下面重新看完了《生死場》。魯迅寫道:
“周圍像死一般寂靜,聽慣了的鄰人的談話聲沒有了,食物的叫賣聲也沒有了,不過偶有遠遠的幾聲犬吠。想起來,英法租界當不是這情形,哈爾濱也不是這情形;我和那里的居人,彼此都懷著不同的心情,住在不同的世界,然而我的心現(xiàn)在卻好像古井中水,不生微波,麻木的寫了以上那些字,這正是奴隸的心!——但是,如果還是擾亂了讀者的心呢?那么,我們還絕不是奴才。”
這一閱讀場景,我是很會意的,因為我也是在燈下重讀《生死場》,也是這種自己在世界之外,或者說在別一個世界的感覺。魯迅當時是和《生死場》的世界處在同一個空間,但是遠隔千里,而我們現(xiàn)在跟《生死場》隔著空間,也隔著時間,遙遠的長河那頭,東北大地上的人忙著生,忙著死——《生死場》原名叫《麥場》,《生死場》是蕭軍后來幫著改的名字,就是因為“忙著生,忙著死”這句話——這句話,最近我還看到有網(wǎng)絡小說引用,這是很有意思的一個現(xiàn)象。
大家都驚嘆說:為什么一個23歲的女子,會寫出如此深重的小說,這確實是除了“天才”,不好解釋的一點。后來劉禾有個說法,說《生死場》是被窄化了,被民族主義給遮擋了。當時魯迅編“奴隸叢書”,幫《八月的鄉(xiāng)村》《生死場》出版,確實是有“要發(fā)出東北淪陷區(qū)的人民的聲音”這樣一個目的。而跟《八月的鄉(xiāng)村》相比,《生死場》的文學價值絕對不在于反映了東北民眾抗日的決心,對吧?
其實《生死場》的好處,我們將胡風批評《生死場》的話反過來讀,就對了。
胡風說:《生死場》的短處和弱點——
第一對于題材的組織力不夠,全篇現(xiàn)的是一些散漫的素描,感不到向著中心的發(fā)展,不能使讀者得到應該能夠得到的緊張的迫力。
第二,在人物底描寫里面,綜合的想象的加工非常不夠,個別的看來,她底人物是活的,但每個人物底性格都不凸出,不大普遍,不能夠明確的跳躍在讀者底前面。
第三,語法句法太特別了,有的是因為作者所要表現(xiàn)的新鮮的意境,有的是由于被采用的方言,但多數(shù)都卻只是因為對于修辭的錘煉不夠。
胡風說的這三條,其實就是要把蕭紅馴化成一個嚴絲合縫的非常規(guī)范的左翼作家。你還記得嗎?當時我們說丁玲《水》的時候,《水》也是被批評說沒有體現(xiàn)黨的領導,過于描寫了民眾自發(fā)的憤怒。說《生死場》里的人物性格不凸出不普遍,實際上就是說它不夠典型。什么叫典型?這個后面有很大的文學問題。
最扯的,就是說“語法句法太特別了”,說這是蕭紅“對于修辭的錘煉不夠”。誠然,廿三歲的蕭紅,文筆絕對還談不上成熟,比起后來的《呼蘭河傳》,情緒沒有那么純凈,文字也沒有那么干凈,但是恰恰是她的這種寫法,給了后續(xù)無窮的希望。《紅樓夢》里面大觀園姐妹連詩,讓沒文化的不認字的王熙鳳起第一句。王熙鳳說“一夜北風緊”,大家說這句話雖然粗,但是“給后人留下了多少余地”。蕭紅就是這樣,《生死場》就是留下多少余地。
我講一講這次重讀《生死場》之后的一個感受,特別有意思的地方在哪里?鄉(xiāng)土文學一般來說都會有一個特點,就是開篇會做介紹,比如說我要寫的是什么地方,這個地方怎么樣,寫的這個人是個什么身份,什么性格,等等。因為鄉(xiāng)土文學,他要預設外鄉(xiāng)讀者不了解這一方土地,需要用介紹把讀者帶進去。
魯迅的短篇小說里面固然有這種描寫,比如說阿Q,先寫他的行狀,“優(yōu)勝記略”“續(xù)優(yōu)勝記略”什么的,用一個一些細節(jié)來描述他的性格,光是名字就寫了一章。沈從文《邊城》一開始寫地理環(huán)境,寫老船夫怎么待客的,還有翠翠怎么樣看世界,這些都是前面的一個鋪墊,后來《長河》也是這樣,到了汪曾祺這里就更明顯了,他能將前面差不多三分之一都寫成風俗畫。
但是蕭紅不是這樣,雖然《生死場》也能夠劃到鄉(xiāng)土文學的范疇當中去,但是你發(fā)現(xiàn)沒有,它一開始就是把你帶進去的,每個人物作者不介紹,就好像是一個人念念叨叨的,在回顧自己的故鄉(xiāng)里面,各種各樣人的狀態(tài)。她想起來她就說,不需要跟你介紹這個人跟那個人什么關系,你看得出來就看,你看不出來也沒有關系,但是《生死場》的行文里有著濃烈的情緒,可以把人一直帶著走。
這就是說,蕭紅的小說一開始就帶有強烈的詩化色彩。我們知道詩歌創(chuàng)作是不會給你一個整體的架構的,它一定是快刀插入,做一個截面的展示。蕭紅的這篇《生死場》實際上就是做到這一點。這一點,從現(xiàn)代小說技術上來說,其實是一個很大的躍進,我們知道中國古代小說喜歡一開篇就交代某地有個什么人,這個人怎么地,這一點被鄉(xiāng)土寫作很大程度保留下來了,我們看中國的鄉(xiāng)土小說,不管好壞,總是覺得它的現(xiàn)代感不夠——現(xiàn)代感就是西方小說感,它沒有掙脫古代小說的某種套路,而蕭紅的《生死場》則不然,我覺得它非常現(xiàn)代。我們不管政治意識形態(tài),我們就從書寫架構來說,不管是丁玲的《莎菲女士的日記》,還是蕭紅的《生死場》,它們都是更現(xiàn)代的文體,都是非常自我的,能夠帶著人的情緒往前走的,而不是說循規(guī)蹈矩地去鋪設一個架構。
這一點區(qū)別,可能跟性別有關,但是其實也跟才氣有關。我覺得蕭紅的《生死場》在這方面是特別可貴的。所以不要說它的主題怎么樣,或者說思想高度怎么樣,單就技術而言,蕭紅在1930年代已經(jīng)是出類拔萃的了。如果不是張愛玲出現(xiàn)的話,還真不見得有另外一個女作家能跟她相提并論。當然“蕭紅還是張愛玲”,這是永恒的話題,我們留到以后,或者是下個月我們讀張愛玲的時候,我們再來談。
好,這就是今天的早茶夜讀之小說民國,我們下周再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