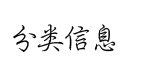李修文比我想象中溫和很多。
最近三年,他帶著一系列動(dòng)人心魄的小人物故事“殺回”當(dāng)代文壇,聲稱要為那些被生活打倒在地的人樹碑立傳,你幾乎以為,他就是那個(gè)要和風(fēng)車再戰(zhàn)三百回的“堂吉訶德”。
在深圳覓書店見到的李修文,卻平實(shí)得有點(diǎn)出人意料。
李修文現(xiàn)為湖北省作協(xié)主席,也曾做過編劇、影視監(jiān)制。著有《滴淚痣》《捆綁上天堂》等多部小說,曾獲茅盾文學(xué)獎(jiǎng)新人獎(jiǎng)、春天文學(xué)獎(jiǎng)等多種獎(jiǎng)項(xiàng),散文集《山河袈裟》獲第七屆魯迅文學(xué)獎(jiǎng)。擔(dān)任編劇和監(jiān)制的作品有《十送紅軍》《瘋狂的外星人》等,編劇作品曾獲電視劇飛天獎(jiǎng)、大眾電視金鷹獎(jiǎng)。
從2003年的《捆綁上天堂》到2017年的《山河袈裟》,中間空了整整14年,當(dāng)被問到“為何離開又為何歸來(lái)”這樣的大問題,李修文嘿嘿一笑:“離開”是因?yàn)閷懖幌氯チ耍劣凇皻w來(lái)”,因?yàn)橐恢鼻倪溥湓趯懀菊劜簧习 ?/p>
而那空缺的十幾年時(shí)光,被李修文稱作“浪蕩的11年”。他在無(wú)數(shù)個(gè)劇組摸爬滾打,在大雪紛飛的冬夜整夜不眠,發(fā)過電,做過場(chǎng)工,趴在河灘上寫劇本,被人忽悠、灌醉……橄欖百煉成渣,李修文把自己煉成了粗糲的江湖小人物,之后,無(wú)數(shù)的小人物傳奇從他筆下涌了出來(lái)。
他沒有太強(qiáng)的“成功學(xué)”焦慮。不管是16年前告別小說,背著一只行囊出門混世界;還是把運(yùn)作了七八年的影視工作室關(guān)掉,重新回到文學(xué)的書桌旁,拿起、放下,他都只是為了自己“想要的一場(chǎng)人生”。
從江湖回到廟堂,如今做了湖北省作協(xié)主席的李修文,依然沒有任何的身份感。他說:你再忙,忙得過歐陽(yáng)修,忙得過蘇東坡?沒有人設(shè),就是最好的人設(shè),李修文清晰地知道,他要做的,只是維護(hù)好一個(gè)作家的根本和體面。
難得的是,這個(gè)13歲就在《當(dāng)代作家》發(fā)表小說、因?qū)懽鞅槐K蜕洗髮W(xué)的大才子,也一點(diǎn)不自戀。一個(gè)讀者因《山河袈裟》改變?nèi)松墓适拢湍茏屗p淚潸然。那是因?yàn)椋麖奈锤呖醋约旱膶懽鳎举|(zhì)上,他是一個(gè)只為自己而寫的作家。
更別提他的理性,甚少情緒化,完全不憤怒……
這個(gè)世界充滿了誤解。
李修文如是,他最近的新書《致江東父老》,亦如是。
▲ 李修文《致江東父老》 湖南文藝出版社 2019年9月
這些文字,究竟是散文還是小說?
那些像《聊齋》一樣的故事,是真的嗎?
為什么要給小人物立傳?
你到底要挑戰(zhàn)什么……
在成都、武漢、長(zhǎng)沙、深圳,李修文一次又一次面對(duì)這些問題,他不疾不徐,重申再重申。
或許因?yàn)椋@些探討中,包含著他作為一個(gè)寫作者,最珍貴的文化基因、美學(xué)立場(chǎng),以及他全部的寫作野心。
李修文說,這是一個(gè)神殿倒塌的時(shí)代,但每個(gè)人都可以建自己的廟宇。他自己是從泥土里長(zhǎng)出來(lái)的小人物,所以,他的文學(xué)小廟也只供奉小人物。
采訪中,他一直說,自己受楚文化影響至深。我倒是覺得,他真不是堂吉訶德,他更像千年前汨羅江邊,那個(gè)倔強(qiáng)寫下《天問》的屈原——他希望在自己的文字中復(fù)活的“中國(guó)式面孔”。
1、我開始不信我試圖寫下的文字
深圳商報(bào)《讀書周刊》:最早,你其實(shí)是以小說名世的。作為當(dāng)時(shí)“中國(guó)最年輕的專業(yè)作家”,2002年的《滴淚痣》和2003年的《捆綁上天堂》那時(shí)引起過熱烈反響。可就在人們期待你拿出小說“三部曲”的時(shí)候,你停了筆。為什么?
李修文:我寫那兩個(gè)長(zhǎng)篇的時(shí)候,正是中國(guó)社會(huì)向著一個(gè)物質(zhì)化時(shí)代狂奔的年代,而我所秉持的、對(duì)我的美學(xué)形成強(qiáng)烈影響的古典價(jià)值,正發(fā)生分崩離析的變化,這種變化甚至使我在日常生活里找不到確認(rèn)。而我又是那種人,一定要把我的寫作袒露成生活的樣子,要去遭逢、去驗(yàn)證、去確認(rèn)的那種人。我開始不信我試圖寫下的文字,進(jìn)而影響了我的創(chuàng)作力。
▲《我亦逢場(chǎng)作戲人》插圖(蔡皋 繪)
怎么辦呢?那我就出門去碰一碰,把自己從一個(gè)創(chuàng)作者活回一個(gè)人。于是,我就混了十年的影視圈,跟著一個(gè)個(gè)的劇組去干活,但是也沒有混出什么名堂。那些年,影視界特別亂,好多項(xiàng)目聽上去都是花團(tuán)錦簇,沒兩天,老板就跑路了。
深圳商報(bào)《讀書周刊》:《致江東父老》里的第一個(gè)故事《猿與鶴》,講的就是一個(gè)落魄編劇,那是你自己的故事么?
李修文:那就是我自己啊。這11年,我寫過十個(gè)出頭的劇本,拍出來(lái)的兩三個(gè)而已。我也參與過N多的電影、電視劇的所謂“策劃”,然后絕大部分都不了了之了。幾乎每一次,都是興沖沖地去,最后敗興而歸。
▲《小站秘史》插圖(蔡皋 繪)
2、這個(gè)江湖帶給我很多啟發(fā)
深圳商報(bào)《讀書周刊》:但是這十年給你帶來(lái)了巨大的蛻變?
李修文:更多的是,我和這個(gè)世界建立了某種真正的關(guān)系。
現(xiàn)在的中國(guó)作家被人認(rèn)識(shí),更多在一個(gè)專業(yè)的寫作場(chǎng)域。但我們看看博胡米爾·赫拉巴爾,看看弗朗西斯·斯科特·基·菲茨杰拉德,大量歐美作家在日常生活中都有一個(gè)形象,赫拉巴爾是個(gè)打短工的人,菲茨杰拉德本質(zhì)上就是個(gè)日常生活中的蓋茨比。
我們?cè)倏纯粗袊?guó)古代的文人,他們也不像今天的中國(guó)作家,要么是個(gè)宰相,要么是個(gè)被貶的縣令,要么是個(gè)窮書生,他們?cè)谌粘I町?dāng)中建立了一個(gè)作為“人”的形象。
作為“人”的形象,從哪兒建立的呢?就是在這樣一個(gè)廣袤而浩大的世界上。所以,我想解決這樣一個(gè)問題:我太早就開始了專業(yè)創(chuàng)作,我始終和這個(gè)人間隔膜著。
▲《致江東父老》插圖(蔡皋 繪)
我一直沒有太強(qiáng)的“成功學(xué)”焦慮,也并不認(rèn)為影視界就比文學(xué)界“牛”多少,相反,此時(shí)此刻在中國(guó),你很難找到一個(gè)文化程度這么低的行業(yè)——這不是一句鄙薄的話,這就是它的生命力所在。這個(gè)江湖帶給我很多啟發(fā)。它帶給了我一種迥異于過去的專業(yè)文學(xué)生活的方式,沒有什么文人相輕,開門就要養(yǎng)活一堆人……這種粗糲是一種錘煉,它讓我和這個(gè)世界真正建立起一種關(guān)系。
3、我一直在寫,談不上“回來(lái)”
深圳商報(bào)《讀書周刊》:自從2003年的《捆綁上天堂》之后,你很久沒有新書出版,為什么2017年突然回歸,出版了那么一本《山河袈裟》?
李修文:其實(shí),在做影視編劇、監(jiān)制的11年,我一直在寫,而且從來(lái)沒有一天放棄過對(duì)于什么是文學(xué)、什么是真正的寫作的正信。
我是因?yàn)閷懖怀鲂哪恐械奈膶W(xué),才在外面“浪蕩”了11年。但我時(shí)刻都想寫我心目中想寫的東西,一天也沒放棄過。所以并不是說,我有一天決定不干了,然后來(lái)寫《山河袈裟》和《致江東父老》,不是的,我其實(shí)不斷在寫。
▲ 李修文《山河袈裟》 湖南文藝出版社 2017年1月
包括《致江東父老》里很多篇章,都是我十年前寫的。只是那個(gè)時(shí)候沒有一種文體意識(shí),更多是一種下意識(shí)行為,一種冥冥當(dāng)中想“挽救”自己的下意識(shí)。
我會(huì)擔(dān)心,寫劇本時(shí)間長(zhǎng)了,劇本的語(yǔ)感會(huì)不會(huì)影響到某種純正的、有力量的、靜水深流式的漢語(yǔ)的正當(dāng)?shù)缆罚磕菢右环N語(yǔ)言,我還能不能把它捍衛(wèi)住?于是,我不斷寫一些心目中的作品,來(lái)提醒自己,這個(gè)敏感度不能丟。所以其實(shí)我一直在寫,談不上“回來(lái)”。只是那本書是2017年出版的,僅此而已。
4、簡(jiǎn)單劃分“虛構(gòu)”和“非虛構(gòu)”,是一種罪惡
深圳商報(bào)《讀書周刊》:有人說,2017年以后,“小說家和編劇李修文,變成了散文家李修文。”我當(dāng)然不同意這樣的身份界定,因?yàn)樘摌?gòu)和非虛構(gòu)實(shí)際上界限沒那么分明。我們今天還能說《致江東父老》僅僅是散文嗎?
李修文:諾貝爾文學(xué)獎(jiǎng)得主S.A.阿列克謝耶維奇說過一句話:當(dāng)我行走在風(fēng)中,意味著多少長(zhǎng)篇小說的消失。今天,某種非虛構(gòu)的“神話”還蠻可疑的。好像我們界定了一個(gè)想象中的“非虛構(gòu)”樣貌,但恕我直言,它只是一種現(xiàn)代學(xué)科細(xì)分以來(lái)人類發(fā)明的又一個(gè)新詞匯,包括“散文”。中國(guó)過去哪有什么“散文”,只有一個(gè)東西叫“文章”。“散文”這個(gè)概念從誕生至今,也就90多年歷史,對(duì)于一個(gè)有著3000年文章傳統(tǒng)的國(guó)度,“散文”這個(gè)概念就那么確定無(wú)疑嗎?我們有沒有可能通過今天的寫作,重新召喚和聚集一種中國(guó)式的傳統(tǒng)“文章”的道路在今天這個(gè)時(shí)代的復(fù)活呢?
▲《致江東父老》插圖(蔡皋 繪)
李敬澤的《會(huì)飲記》是我非常喜歡的一本書,它感知到了一個(gè)變化:總體性四分五裂。一切堅(jiān)固的東西都煙消云散了,我們的身體、我們的感官變成了最大的總體性。小說也在變化,散文也在情不自禁地變化,所謂的“虛構(gòu)”和“非虛構(gòu)”都要受到這個(gè)時(shí)代的裹挾。不管你同不同意,過去界定的那些關(guān)于文體的鐵律,都在一點(diǎn)一點(diǎn)地受到碎片化的動(dòng)搖。這個(gè)時(shí)候我嗅到了一個(gè)東西,或者說它成為了我寫作的直覺:我的一趟歷程下來(lái),其中包含著我的狂想、我強(qiáng)烈的想象所產(chǎn)生的事實(shí),它們共同構(gòu)成了一個(gè)作家最大的真實(shí),那就是作家要提供出一個(gè)無(wú)限真實(shí)的精神個(gè)體。這個(gè)精神個(gè)體,可能才是這個(gè)時(shí)代最大的真實(shí)。
我覺得,簡(jiǎn)單地把文章分為“虛構(gòu)”和“非虛構(gòu)”,是一種罪惡。它降低了人們對(duì)于今天這個(gè)時(shí)代的立體認(rèn)知。
5、撕破一切無(wú)法準(zhǔn)確表達(dá)內(nèi)心的文體束縛
深圳商報(bào)《讀書周刊》:我個(gè)人認(rèn)為,和你很多年前的小說相比,最近這兩本書是一種文體的進(jìn)步。但正是文體,也的確成為這兩本書被爭(zhēng)論最多的點(diǎn)。
李修文:我覺得這是一件好事。我無(wú)意借這個(gè)討論去博任何眼球,但我可以非常誠(chéng)實(shí)地說,文體到了今天,真的是要重新認(rèn)識(shí)了。中國(guó)的“文章傳統(tǒng)”何其大,“散文”概念只是“文章傳統(tǒng)”里一個(gè)小小的格子,我們不能在這個(gè)格子里待久了,就把如何待得更舒服、更精致變成了一種王道。我希望用自己的寫作來(lái)提醒大家,有沒有可能重新觸摸中國(guó)式的“文章”道路?
▲《不辭而別傳》插圖(蔡皋 繪)
因?yàn)橹袊?guó)人的情感方式的確和外國(guó)人不一樣,我們的四大名著寫的是內(nèi)心里的明明滅滅、哽咽、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凈;外國(guó)名著寫的是通過人類經(jīng)受的苦難,肯定人類必然有承受和超越苦難的能力,于是人是值得贊美和肯定的。
當(dāng)然,我這樣講,是把西方文學(xué)簡(jiǎn)單化了。但當(dāng)你試圖去總結(jié),一定會(huì)看到,中國(guó)人的情感方式是“眼看它起高樓,眼看它樓塌了”,它是我們?cè)跉v史長(zhǎng)河、在一個(gè)空茫的倫理和體系里求而不得的內(nèi)心的印證。所以,中國(guó)人的歷史雖然是戰(zhàn)勝者寫成的,可戰(zhàn)敗者、柔弱者的聲音,在文學(xué)里頭。
中國(guó)式的“文章”和西方式的“非虛構(gòu)”“散文”不一樣。在我看來(lái),一切無(wú)法準(zhǔn)確表達(dá)內(nèi)心的文體束縛,都應(yīng)該把它撕破。更確切來(lái)講,我寫作,并不是為哪一種文體而寫。我都不在乎,你們還有什么好在乎?
6、我期待荊楚風(fēng)格的復(fù)活
深圳商報(bào)《讀書周刊》:《致江東父老》里有好幾個(gè)故事讓人分不清真實(shí)和虛幻。例如《白楊樹下》,“我”一路走一路說話的表姐早就死了;《魚》的結(jié)尾,一群魚高高躍出水面,把母親從死亡邊緣拉回。這些場(chǎng)景,在現(xiàn)實(shí)生活中顯然不可能存在,該怎么理解它們?
李修文:我確信遇見過這些事。我也知道依科學(xué),是遇不見的,但在我的生命歷程中,它們確實(shí)存在過。包括那條魚,就是我本身的遭遇。我清晰記得那一幕,一群魚像菩薩般從水下跳躍了出來(lái)。那一幕,在許多年里不斷被我回憶起來(lái),它們一次次被我想象、認(rèn)知和建構(gòu),最終,它們呈現(xiàn)出了一個(gè)寫作者意義的真實(shí)。
▲《白楊樹下》插圖(蔡皋 繪)
我來(lái)自一個(gè)自古以來(lái)巫風(fēng)大作之地,一個(gè)產(chǎn)生過屈原《天問》《山鬼》的地方。小時(shí)候,經(jīng)常有一個(gè)老太太攔下我,認(rèn)真地說她死去的兒子昨晚回來(lái)了,帶了米,還挑了滿缸的水,現(xiàn)在又回去了,過段時(shí)間還會(huì)再回來(lái)看她。直到許多年后,穿州過府,我也算是踏足了這世間的不少地方,和死去的表姐隔世相見這樣的事,在家鄉(xiāng)之外的地界還是鮮少能夠聽說。除了在《聊齋志異》里,似乎就只在我的家鄉(xiāng)屢屢發(fā)生。
你生活在那樣一個(gè)人鬼共居、視死如生的環(huán)境中,今天再拿著霍金式的觀點(diǎn)去考察它的真?zhèn)危覀兪怯卸酂o(wú)趣?其實(shí),我在講述這類場(chǎng)景時(shí)所產(chǎn)生的一種迷亂之感,哪怕是想象占據(jù)主導(dǎo)所產(chǎn)生的一種想象,但我認(rèn)為,這就是我心中的真相。對(duì)于一個(gè)作家來(lái)說,我認(rèn)為只有一種真實(shí),就是美學(xué)意義上的真實(shí)。
▲《魚》插圖(蔡皋 繪)
作為一個(gè)楚人的后裔,我期待那種荊楚風(fēng)格的復(fù)活。我希望能從美學(xué)上靠近一種近似于《天問》和《山鬼》的傳統(tǒng);我也希望從氣質(zhì)上寫下一個(gè)個(gè)像項(xiàng)羽和屈原那樣決絕的、并且依然能夠在現(xiàn)代生活中成為我們同路人的人。
7、我后來(lái)寫作,就變成了那個(gè)盲人
深圳商報(bào)《讀書周刊》:這本書寫了那么多小人物,哪一個(gè)人物最接近你心中“江東父老”的樣子?
李修文:這本書里頭,最早寫出來(lái)的是《三過榆林》。我曾經(jīng)在陜西榆林遇見過一個(gè)盲人。當(dāng)這個(gè)盲人在榆林的郊外,非常嚴(yán)肅地告訴我,現(xiàn)在我們不是走在榆林,而是走在華燈初上的十里長(zhǎng)街……他的一生,就是靠這樣安慰自己度過來(lái)的。你告訴我,這種虛構(gòu)對(duì)他來(lái)說,是不是一場(chǎng)巨大的真實(shí)?
▲《窮人唱歌的時(shí)候》插圖(蔡皋 繪)
通過和這個(gè)盲人的相遇,我才知道,中國(guó)大量盲人并不是死于其他疾病,而是死于精神疾病。因?yàn)槊と丝床灰姡欢ㄒ獜?qiáng)烈地想象一個(gè)世界,久而久之,腦中的世界就和身外的世界開始撕扯同一個(gè)肉身,撕扯的過程,很多人會(huì)被擊垮,擊碎,最終死于精神分裂。
所以你問我印象最深的小人物,我想就是他,那個(gè)盲人。他不光是我的一個(gè)寫作對(duì)象,他甚至啟發(fā)了我的寫作。我后來(lái)寫作,就變成了那個(gè)盲人。我一定要把我所構(gòu)建的那個(gè)世界,作為真實(shí)的一部分端出來(lái)。
深圳商報(bào)《讀書周刊》:都是寫小人物,和《山河袈裟》相比,《致江東父老》的不同在哪里?
李修文:《致江東父老》里頭沒有多少大驚小怪的東西。它很大程度上取消了自我,跟隨在我的寫作對(duì)象背后,在沉默地追隨。而且我也有志于用一種最簡(jiǎn)練的字句來(lái)營(yíng)造,或者讓人獲得一種最空茫、最遼闊的氣息。
▲《鐵鍋里的牡丹》插圖(蔡皋 繪)
從文體上,我也做了很多努力。例如《魚》和《白楊樹下》寫得像《聊齋》,《我亦逢場(chǎng)作戲人》我采用了一個(gè)“說書人”的調(diào)門,《猿與鶴》采用的是一種結(jié)構(gòu)上的回環(huán)……這些文體嘗試是我有意為之,是想更多地取消自己,更加貼切到寫作的對(duì)象。
8、我內(nèi)心沒那么多“人設(shè)”
深圳商報(bào)《讀書周刊》:2018年你當(dāng)選湖北省作協(xié)主席,作為一個(gè)混了那么多年江湖的作家,如今的身份和你的初心會(huì)有碰撞么?
李修文:沒有任何的對(duì)撞。我內(nèi)心沒有那么多“人設(shè)”。我一直提醒自己,一定要輕看“人設(shè)”,千萬(wàn)不要被這些反智的東西囚禁得更深。
▲李修文
擔(dān)任作協(xié)主席,對(duì)自己的創(chuàng)作精力當(dāng)然有影響,但影響也沒那么大,我經(jīng)常舉個(gè)例子:你再忙,忙得過歐陽(yáng)修,忙得過蘇東坡?這就是那“浪蕩”的11年帶給我的。我在劇組里,連場(chǎng)工都做過了,有一年在重慶的忠縣拍戲,大雪紛飛,我坐在一個(gè)果林里頭,守著發(fā)電機(jī)守了一晚上。作協(xié)主席這個(gè)事,總不會(huì)比那個(gè)更苦吧?
9、我的廟里供的都是小人物
深圳商報(bào)《讀書周刊》:遇到過讓你印象深刻的讀者嗎?
李修文:前不久我遇到一個(gè)讀者。她曾經(jīng)是個(gè)生物系本科生,看完《山河袈裟》,想轉(zhuǎn)戲劇,于是開始了漫長(zhǎng)的考研生涯。她告訴我,每一次撐不下去的時(shí)候,就得看《山河袈裟》,直到發(fā)榜前。后來(lái),她如愿考上了中央戲劇學(xué)院的戲劇文學(xué)研究生。我不是一個(gè)太情緒化的人,但聽完這個(gè)讀者的故事,當(dāng)時(shí)我雙淚潸然。
我從來(lái)沒有那么高看自己的寫作,也不覺得我的寫作會(huì)重要到什么地步。對(duì)我來(lái)說,寫作是一種自救,不管人們?cè)趺纯矗叶紩?huì)寫出來(lái),不在乎重不重要。但就是在這種一個(gè)人狂奔的路上,居然還曾經(jīng)安慰過一個(gè)人,參與了她的人生,我覺得莫大的幸福,還有什么比這個(gè)和讀者之間的溝通,更讓一個(gè)作家有尊嚴(yán)感呢?
▲《在春天里哭泣》插圖(蔡皋 繪)
現(xiàn)在,每個(gè)人都陳詞濫調(diào)地說:神殿倒塌了。但新的神殿在哪里呢?大雄寶殿倒塌了,土地廟還在啊。你有沒有能力,建一座自己的小廟呢?然后,招來(lái)一點(diǎn)點(diǎn)自己小廟里的信眾呢?
深圳商報(bào)《讀書周刊》:可否這樣說,你的寫作就是建廟的過程?
李修文:我在建我自己的一座廟宇,我的廟里供的都是小人物。
10、下一本書是關(guān)于中國(guó)古詩(shī)詞的詩(shī)話
深圳商報(bào)《讀書周刊》:下一步創(chuàng)作計(jì)劃是什么?
李修文:我在寫一本關(guān)于中國(guó)古詩(shī)詞的詩(shī)話,還有一本小說集。
我一直喜歡中國(guó)的古典詩(shī)詞,但我也特別不滿意,現(xiàn)在很多中國(guó)人對(duì)于詩(shī)詞技法上的探討和研究。
▲《何似在人間》插圖(蔡皋 繪)
在我們中國(guó)人的一生中,在我們?cè)S許多多的關(guān)口和要害,總是猝不及防地、撲面而來(lái)地,和我們?cè)谠?shī)詞里頭見過的情景遭遇。所以中國(guó)詩(shī)詞對(duì)中國(guó)人來(lái)講,首先不是個(gè)學(xué)問,它首先是我們的出處和來(lái)歷,它就是我們的生命本身。
到底有哪一些詩(shī)詞它,在什么樣的時(shí)刻,以什么樣的面目,見證過我們的生活,降臨過我們的生活,又安慰過我們的生活?我想要寫這樣的“人與詩(shī)詞的相遇”。
(本文由出版社授權(quán)轉(zhuǎn)發(fā),插圖均為《致江東父老》插畫,由繪本畫家蔡皋繪制,出版方供圖)
文 / 劉悠揚(yáng),編 / 俎燚楠